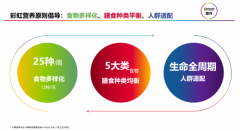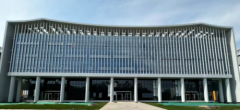嘉峪关前的白杨树:一个甲子前的种树故事
嘉峪关前的白杨树
在312国道嘉峪关段的路边,并排站立着八棵树,紧挨着一座砂质小高地。穿过马路不远处,就是高大的嘉峪关古城楼。在当今绿树成荫的嘉峪关市,这八棵树毫不起眼,要不是树旁纪念碑的提示,在旁人看来就只是广袤的西北大地常见的白杨而已。可是,这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物。
时间还要上溯到1952年。那时候的嘉峪关市还不存在,只有一座荒废已久的孤零零的古城楼,矗立在祁连山一处巨大的豁口中,周围全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。一条砂土筑起的大路,从河西走廊的东边,一路向新疆方向延伸,从东边的天地无尽处,隐没在西边的天地无尽处。
初春时分,大风卷起砂石,天地一派混沌。这时,新中国第一代筑路工人郑占乾,萌生了一个虽宏大却似乎不怎么现实的愿望:给路边栽树。
眼下没有劳动力,只有几名家属妇女,包括自己有身孕的妻子。也没有劳动工具,只有捅炉钎和铁铲。凿开坚硬的砂石,将十几棵瘦弱的杨树苗栽植进去,过了几天,居然有八棵树苗活了,还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。对这些身在荒漠的劳动者来说,最大的鼓舞莫过于生命的诞生和成长。从此,他们像维护公路、养育儿女一样精心照顾这八棵树,每日每时,心心念念。
时间过去了一个甲子。前年夏天,嘉峪关公路局杨局长带我去拜访郑占乾老人,并给老人颁发五十六年党龄的纪念章。老人居住在单位的家属院里,屋内陈设简朴,但干净整洁。老人身穿中山装,茶几上端放着一份几十年来每日必读的《人民日报》,一旁的果盘里搁着刚从树上摘下的杏子,金黄金黄的。在家人的帮助下,他将纪念章端端正正戴在胸前。年过九旬的老人了,在戈壁滩做了几十年的野外养路工,在他的身上丝毫看不出沧桑倦怠,眉宇间闪射着的是坚毅和自豪。子从父业的大儿子垂手站立一旁,我请他坐下,他笑笑,依然站立着。他也是八棵树的见证者,母亲怀着他,跟着父亲,一同栽下了这八棵树。如今他也是“奔七”的人了。
说起当年栽植八棵树的故事,郑占乾老人的话不多,目光清澈,语气平淡。他反复强调说,这都是工友们的功劳,都是来自组织上的支持和关爱,他只是做了一个工人该做的事情。
八棵树的意义体现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。祁连山深处的镜铁山发现了铁矿,这是我国钢铁工业的一件大事。厂址和职工生活区选在嘉峪关的戈壁滩上,距离矿山八十公里路程,修建一条铁矿石运输专线公路迫在眉睫。这段公路所经之地,少部分是戈壁滩,大部分在山区。在吊达坂一带,海拔都在四千米以上,或终年积雪,或永久冻土。过了吊达坂,到二指哈拉的几十公里,全是高山峡谷,飞石悬空,湍流喧闹。别说那时候,当下这段路已经变成等级公路,车技差一些的司机仍然不敢在这种路段驾车行驶。筑路工具呢?没有大型机械,只有铁镐、铁锹、抬筐,还有少量畜力车。就靠这样简陋的工具,筑路大军凭借着对国家的一腔忠勇,炸石开山,人力搬运土石方,昼夜奋战,在高山缺氧环境中克服物资供应之不足,只用了两个月时间,就打通了一条运输铁矿石的专用公路。
八棵普通的白杨树,不仅为一条生命线一样重要的公路敲响了开场锣鼓,事实上也是一座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开始。大西北许多新兴城市的建设堪称“无中生有”,嘉峪关就是这样一座城市。嘉峪关的名字在明朝已经声名远播,但其功能主要在军事方面。失去军事功能之后,就只是酒泉管辖下的一处古迹了。铁矿的发现,激活了这座“天下第一雄关”。一时间,筑路者,开矿者,各行各业的建设者,随行的家属,从祖国各地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乃至步行,涌向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,成为嘉峪关的第一批建设者和居民。城市因矿山而诞生,那么,连接城市与矿区的道路便成为重中之重了。
一条道路固然短时间可以打通,但维护道路的正常运行,却是经年累月的功课。郑占乾与他所在的公路段的工友们,在此后的数十年中,日复日,夜复夜,把青春年华,把人生理想,全部交给了这条道路。又是沙漠戈壁,又是高寒山区,又是简易公路,修筑的难度大,维护的难度更大。路上行走的都是载重卡车,路面质地粗糙,极易损毁。冬天大雪封路,开春路面翻浆,夏秋季洪水冲毁公路,困难和危险是道班工人的家常便饭。
国家财力有限,道班工人不多,道路必须保持畅通。大家一年四季大多时间都坚守在岗位上,常常一两个月回一趟家。而回家之路更为艰难,或者搭乘拉运矿石的卡车,或者徒步,仅在路上就要耗去一两天时间。所谓道班,也只是在路边挖一个地窝子,能够防御野兽和风雪罢了。日常所需食品,依靠往来卡车捎带,饮用水则要到深沟去取,取一趟水需要耗费半天时间。更困难的是护路工具过于简陋,最初只是一些简单劳动工具,劳动效率很低,去一趟工地,晚上回不了道班,就只能在野外露宿。但工人们没有“等靠要”,而是自力更生,向发明创新要劳动效率。郑占乾和工友们发明了一种畜力刮路机,用一些废旧钢材木料,做成耙耧式样,套上毛驴,刮平路面。这种机械,后来推广到西北的许多公路段,使用了许多年。嘉峪关的公路博物馆里还陈列着这样的机械,让人既为前辈道班工人的聪明才智由衷敬佩,也为他们所经过的艰难岁月而心潮起伏。